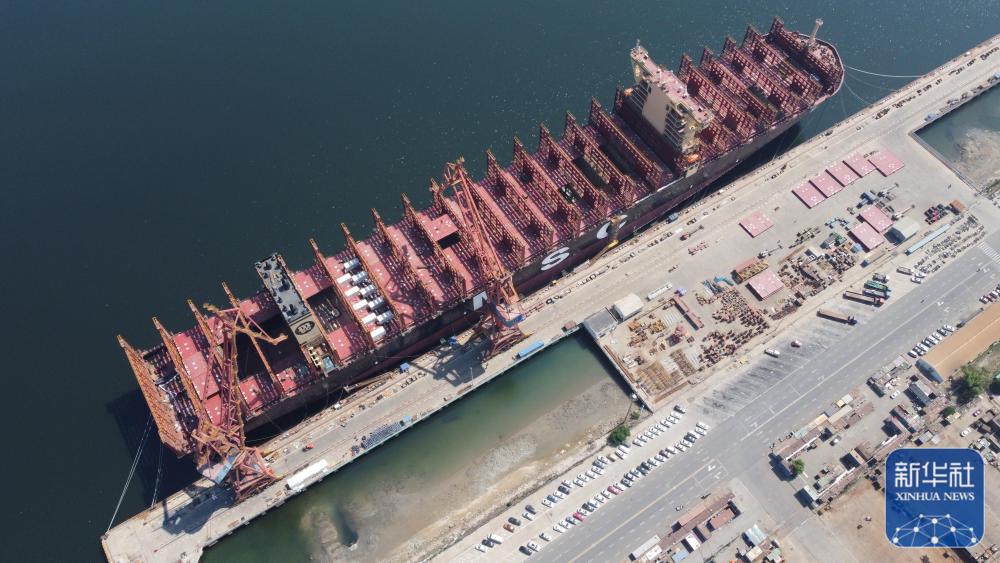“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母校厦门大学的海滨,在沙滩上悄悄落泪,那一定是我想念着那些爱我但不在人世的老师,其中首先是郑老师。他是一个真正影响过我,真正在我的心坎中投下过宝石的人。他写给我那么多书信,可惜大部分都留在沧海的那一边。尽管如此,他的名字还是伴随着我浪迹天涯。无论是飞行在白云深处,还是航行在波罗的海的蓝水中间,我都会突然想起他的名字。在天地宇宙的博大苍茫之中,他的名字和其他几个温馨的名字就是我的故乡。”这是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写在《缅怀郑朝宗老师》中的一段话。我在此引用,是想说明那些真正的学者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少知而减弱他们的地位与影响。
郑朝宗先生一九一二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现代小说博士学位,归国后长期执掌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系郑先生的高年级学长,迨一九四〇年代初,俩人又同住上海,过从甚密,遂成终生好友。一九四八年《围城》出版后,有人妄作批评,郑先生即发表《〈围城〉与〈汤姆·琼斯〉》一文予以公允评论,钱锺书因此称郑先生为《围城》的“赏音最早者”。一九七九年钱锺书先生的大著《管锥编》出版,郑先生即在厦门大学招收《管锥编》研究生,开“钱学”研究之先路。一九八〇年郑朝宗评论《管锥编》的著名论文《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发表后,钱锺书特意致信说:“感激之情,不亚于惭愧之情,而叹服之情,又不亚于感激之情。”和诸多前辈学者一样,郑先生也是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典范。就作家而言,郑先生特别擅长散文创作,出版有《护花小集》《梦痕录》《海滨感旧录》等散文集。就学术而言,郑先生出版有《小说新论》《欧洲十大名著及作者》《西洋文学史》等专著或教材,编译过《德莱登戏剧论文选》,并和他的研究生合作出版了《〈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恩师俊才先生和郑先生的联系也始于他编选《林纾研究资料》时期。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张老师了解到福州市文联主办的刊物《榕花》上刊有一篇评论林纾的文章《翻译界的奇人》,作者是郑朝宗,便向薛绥之先生做了汇报。薛先生听后立即指示:郑先生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是国内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的文章务必找到,最好能收到咱们编的书中。于是张老师便冒昧地给郑先生写信索要此文(信寄厦大中文系)。但郑先生并无回信。一连写了两三封信,郑先生始回信并寄来此文。在回信中郑先生说此文属一般的杂谈介绍之文,不适合收入你们的研究资料之中,所以一直未寄。郑先生此文后来确实未收入《林纾研究资料》之中,但张老师由此却与郑先生建立了联系,以后他编成的各种单篇林纾资料都会先寄郑先生征求意见。到了一九八三年六月,张老师和薛先生共同署名编选的《林纾研究资料》正式出版了。薛先生想找一个人写篇评论向学界推介此书,考虑到钱锺书先生曾说过研究林纾须既通西文又通古文,他们觉得最好能请郑先生来写此文。这样,张老师又冒昧地给郑先生写信提出请求。郑先生的第一封信今已不存,这样保存下来的郑先生写给张老师的前三封信都是因写这篇评论而发的。现将这三封信依次介绍如下。第一封信写在厦门大学的信纸上,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资料图)
(资料图)
俊才同志:
大札及惠赠《林纾研究资料》一书早已收到,谢谢。我因患高血压病,卧床数月,致稽裁答,敬祈原谅。
琴南先生系本省现代开风气之先的一大人物,其所作诗文及翻译小说,大部分均有重大艺术价值,自鲁迅以下无不受其影响。过去有些人只因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便把他一笔抹杀,给予种种丑诋,这是以一眚掩大德的不公正行为,无足称道。对于这样一位文艺界伟人,我们福建人熟视无睹,而林公的子孙也大都属于“不克家”之流,遂使他的名字几于湮没!现在竟由外省人薛绥之先生和您来为他主持公道,我曾告诉责任编辑陈公正同志这是“闽人之羞”!当然,钱锺书先生写的那篇《林纾的翻译》,已在一个方面为林公讲了公道话,使谬悠之口不敢再妄肆雌黄了。
承您好意推荐我给这本研究资料写篇评介文章,我自然很愿意。但因久病体羸,不敢多看书,资料未及细看,未便贸然操管。请稍假以时日如何?
听说您已著有《林纾评传》一书,不知何日可问世?
匆肃,即颂著祺!
郑朝宗 四月五日
第二封信写在传统的竖式信纸上,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信中告知张老师书评已写就,并附赠一册他带领他的研究生共同撰写的“钱学”研究大著《〈管锥编〉研究论文集》:
俊才同志:
四月间接奉大札,嘱写书评,因病兼忙,无由实现。国庆前夕得数日之暇,急草一篇,题作《评〈林纾研究资料〉兼论林纾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共五千余字,遵台命投本省刊物《福建论坛》,大约年底可发表。一俟出刊,即当奉呈请教。
附寄拙编《〈管锥篇〉研究论文集》,到乞登入。
专肃,即颂著祺。
郑朝宗 十月廿四日
第三封信仍写在传统的竖式信纸上,时间是一九八五年的元旦:
俊才同志:
新岁伊始,敬祝健康愉快!《福建论坛》第六期已出版,附寄一本供评骘。拙作中某些公正之颂词被降低调子,林译佳例亦被删去以省篇幅,编辑同志有此权力,只好听之。今后我仍将为引起闽人对林纾一生成就之重视而贡献绵力,愿与足下共勉之。
专肃,即颂著祺。
郑朝宗 元月一日
人世间有些事是永远无法逆料的,因而它给人造成的遗憾也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请郑先生给《林纾研究资料》写评论是薛先生的主意,可郑先生告知评论已经发表的信件发出仅仅半个月后,薛先生却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辞世。据张老师说,薛先生的身体本来不错,但他的工作太紧张了。一九八四年下半年,薛先生已经从聊城师院调至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工作。到此年年底,薛先生同时忙碌着三件事:一是带领他的助手为长达八十万字的《鲁迅杂文词典》定稿,他审阅,助手分别负责修改和核对引文;二是应邀审阅山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并主持答辩;三是协助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的领导制定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如此超负荷地工作,已使薛先生的身体感到不适,但他未在意,结果在赴山东大学开会途中病发,虽然当即送往医院,但两天后竟不治身亡。薛先生突然辞世后,张老师和他的同学们都迅即赶赴济南协助治丧。薛先生的后事料理完毕,张老师方给郑先生回信并报告了薛先生辞世的消息。郑先生接信后也立即复信,这就是张老师保存的郑先生第四封来信,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俊才同志:
捧读大札,惊悉薛绥之先生不幸因病仙逝,老成凋谢,曷胜哀悼!我与薛先生虽无一面之缘,但耳名已久,又曾拜读所编之书,深佩其治学严谨,对后进大力提携,此种精神将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逝者已矣,今后兴学重担落在中青年学者肩上,相信英俊如兄,必能尽传薪之职,使薛先生含笑于九京也。
我患高血压病已数年,时作时愈,家人细心维护,得延残喘至今,然亦惫不能胜,徒食粟而已,知注特告。
新春瞬届,希注意摄卫。
专肃,即颂著祺
郑朝宗 一月卅日
郑先生的这两封信前后相隔仅半个月,信纸书写格式相同,但信札的内容读来却令人唏嘘掩面。上辈学者之间的惺惺相惜,犹如霁月光风,照亮后学。在张老师保存的郑先生第一次来信中,郑先生即有这样一句问话:“听说您已著有《林纾评传》一书,不知何日可问世?”在这句问话旁边,张老师当年整理这些书信时曾加了这样一段附注:“大约是陈公正先生转告说的,其实不是‘评传’,而是‘论稿’。不过倒真想写个‘评传’,‘论稿’就不搞了。现在借备课之机,广泛看各种‘评传’,以资借鉴。”在这封伤悼薛先生猝逝的来信中,郑先生又说:“逝者已矣,今后兴学重担落在中青年学者肩上,相信英俊如兄,必能尽传薪之职,使薛先生含笑于九京也。”薛先生辞世前,张老师已就《林纾评传》的写作计划与薛先生沟通过,薛先生嘱咐他抓紧完成。薛先生辞世后,郑先生的谆谆教诲更使他不敢稍有懈怠。他那时刚到河北师大任教不久,在教学上尚属新手。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全部用在教学上,一到晚间便趁夜深人静之时伏案写作,至一九八六年底,一部二十六万余字的《林纾评传》书稿就完成了。书稿完成之后,张老师又想到了郑先生,想到了郑先生对这部书稿的牵挂,因此他再次给郑先生去信,想请郑先生在身体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帮助审阅一下书稿,如果质量能达到出版要求,则请郑先生赐一篇序文。郑先生接信后要求张老师先把书稿寄过去,他阅读之后再作决定。这样,到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四日,郑先生将书稿与写好的序言一并寄回。同时寄来一信,这是张老师保存的郑先生的第五封来信:
俊才同志:
大作《林纾评传》拜读讫,序文于昨日寄上,想可与此札同时到达。衰病缠绵,不耐久坐,勉强操管,潦草特甚,敬祈原谅。大作力透纸背,可知用力甚勤,无任钦佩。关于短篇小说部分,著墨微嫌过多,稍近烦琐,能否稍加精减?余不一一。
专布即颂文祺
郑朝宗 九月二十四日
此信寄出后,郑先生前往福州料理私事。其间据友人告知序文中提及的王元龙联句原文,又专复张老师一函订正。该信写在随身携带的厦门大学信纸上。内容如下:
俊才同志:
两星期前寄上《林纾评传》稿及拙作序文,谅已到达。顷来福州料理私事,明日即返厦。据此间友人告知:王元龙所书联句原文是“座上岂容凉血辈,此间大有热心人”,前函有误,请即更正。
专布,即颂秋祺
郑朝宗 十月十七日
张老师撰写的《林纾评传》一九八七年就定稿了,但由于受商业化思潮的影响,迟至一九九二年才由他的母校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即获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好评,至二〇〇七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订本。无论是在初版本还是增订本的后记中,张老师都郑重地写下他对郑朝宗先生的感谢和思念。在《林纾评传》的初版(南开大学版)后记中张老师写道:“我尤为感念的是为此书写序的郑朝宗先生。我与郑先生至今尚未谋及一面,但在衰病缠绵不耐久坐的情况下,他不仅及时审阅了全部书稿,还撰写了对后学颇多奖掖之辞的序言。不才如我,何以报答诸师友的如此厚爱和关怀!”在《林纾评传》的增订版(中华书局版)的跋文中张老师又继续写道:“《林纾评传》初版本的序言,是著名学者郑朝宗先生写的。这次我保留了下来。不是因为郑先生在序言中对我颇多奖掖之词,而是因为那序是郑先生在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况下写成的。而我,不仅那时与郑先生未谋及一面,而且直到郑先生辞世也未能与他谋及一面。这是我一个永久的悔,留着这个序,是我对郑先生的一点忆念。”
对先生们最好的忆念,便是恪尽“传薪之职”,使得“治学严谨,提携后进”的精神永得与日月争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十年来我的恩师俊才先生循着前辈们的足印,在这条绵延不绝的传承路上初心如炬,艰辛跋涉,勇毅向前。《林纾评传》之后,张老师还陆续出版了《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坚守与困惑》《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叩问现代的消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等学术著作。吾师有此学行,亦可告慰他一生感佩的诸位恩师了。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
来源:《上海文学》原标题:恩师书札